乐与诗在中国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一方面它们水乳交融,是呈现中国艺术“有域无界”特征的主要代表;另一方面,与其他文化形式相比,诗与乐的关系更具持久性,形成了独特的“音乐文学”形态。本文使用“乐”,而不以“音乐”代之,是因为中国古代“乐”的内涵和外延都与现代意义上的“音乐”不完全一致。概而言之,中国古“乐”是“礼乐之乐”与“音乐之乐”的合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一直推崇的“诗乐一体”实际上就已规定了中国音乐文学应是道德与审美、功利与非功利等多重因素的结合体。从乐学观念转变的角度观照文学潮流的演进,有助于从更为丰富多元的维度研究古代文学的发展历程,避免只从文学学科自身讨论文学问题产生的弊端,这种思路同样适用于清代诗学研究。
清代乐学的实学化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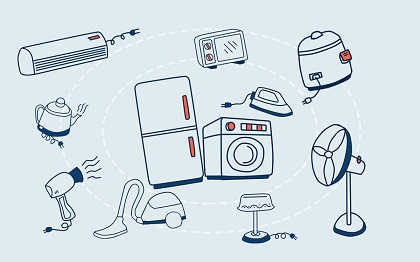 (相关资料图)
(相关资料图)
清代可说是古代乐学实学化潮流的完结期。清代乐学在保留了教化、道德等因素的前提下,也表现出更重视“情”“俗”和“去神秘化”的倾向。
首先,清代乐学注重对自然情感的认同。重视自然情感早在嵇康《声无哀乐论》中便已初露端倪,到了明代,这种趋势在心学的助力下得到新的发展。沿着这个路径,清代乐学进一步将情感因素从教化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这在戏曲演唱理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徐大椿在《乐府传声·曲情》中说“唱曲之法,不但声之宜讲,而得曲之情为尤重”。世俗文艺尤其是戏曲在明清两代的勃兴,改变了以往高雅音乐板起脸宣扬教化的固有套路,观众喜闻乐见成为音乐和戏曲创作者关注的首要问题。
其次,通俗与高雅的界限被消解了。俗与雅的问题是各个时代的文学艺术领域常谈常新的话题,这两个概念通常没有非常清晰明确的界限,很多时候可以互相转化。清代乐学在这一问题上持论非常通达,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包括毛奇龄、江永、徐大椿、徐养沅、李塨等。毛奇龄的《竟山乐录》、江永的《律吕新论》、徐大椿的《乐府传声》、徐养沅的《律吕臆说》、李塨的《学乐录》等著述,都主张雅俗融通,提出了“明乎俗乐之理,而后可求雅乐”“今乐犹古乐”等观念。难能可贵的是,以李塨为代表的清代乐学家肯定“番乐”或“夷乐”的价值,为西洋现代音乐在中国的落地生根提供了理论支撑。
最后,清代乐学表现出“去神秘化”倾向。清代以前的音乐观念,在音乐起源、功能等问题上,往往带有神秘色彩。到了清代,这种情况发生了深度转变。这不仅与雅乐的式微、律学的逐渐成熟有关,也与清人开始“睁眼看世界”的理性倾向密不可分。毛奇龄是较早涉及这方面问题的学者。在他看来,一直以来对音乐乃至五声、十二律等问题的认识,往往“神奇窈眇”,实际上“与声律之事绝不相关”(《竟山乐录》)。受学于毛奇龄的李塨认为,西洋的历法、算法值得肯定,且与中华声律之学相通,进而号召重振中华律学,将其视为“中华实学”的代表。
由此可见,清代乐学带有明显的实学化特征,并逐渐表现出从传统乐学向律学转型的趋势。由于历史原因,清代音乐实践的具体情形现在难以复原,但从理论层面推测,其在实践层面的表情、尚俗、去神秘化倾向应当更加突出。可以说,无论是礼还是乐,清代都呈现出明显的实学化、客观化趋势。
“诗乐一理”观念的瓦解
清代乐学的实学化构成了一种潜在的文化氛围,受其影响的音乐文学表现出了诸多不同于以往的特质。由于这个问题涉及范围较大,为使讨论更具针对性,笔者主要选择音乐文学中的诗歌作为考察对象。清代诗歌表现出回归文学自身的发展趋势。清代诗坛出现了神韵派(王士祯)、格调派(沈德潜)、性灵派(袁枚)、肌理派(翁方纲)等诗歌流派,这些流派大都注重对诗艺的探索。一直以来,学界对清诗的态度不够明朗,或将其看成经学的衍生物,或视其为古代诗歌发展的尾声。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提出:“盖由清代文学而言,也是包罗万象兼有以前各代的特点的。”“包罗万象”本是一件好事,但文学史书写强调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评价“一代之文学”的重要标准,这不仅要求新的文学样式要不断涌现,更要求固有文学样式要体现出新的美学风貌。就清代诗歌而言,若单纯从思想内容、审美境界等方面审视,特点的确不够突出,难以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但若从音乐文学角度考察,则会发现其事件价值大于审美价值,它代表了中国古代礼乐传统与诗歌关系的空前断裂,也表明“音乐之乐”对诗歌的影响进入了新阶段。
清代乐学的客观化极大压缩了“礼乐之乐”的存在空间,潜在地为文学的真正自觉提供了条件。清初王夫之仍主张“诗乐一理”,客观来说,这一观点已属于倡导诗与“礼乐之乐”关系的尾声了。他在《张子正蒙注》中称“正《雅》直言功德,变《雅》正言得失,异于《风》之隐谲,故谓之《雅》,与乐器之雅同义。即此以明《诗》《乐》之理一”,这种说法仍囿于传统话语体系,并无多少新意可言。以此为理论起点,王夫之进一步提出“明于乐者,可以论诗”(《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序》)、“诗与乐相为表里”(《读四书大全说》),所以他所说的“乐”应属于“礼乐之乐”的范围。这种观点在清初的时代背景下出现情有可原,一是源于王夫之对汉族雅化文化体系的坚守,二是符合他儒学宗师的身份。但这种倡导产生的影响有限,相反,清代学者更多围绕“音乐之乐”讨论作诗之法。黄宗羲在《黄孚先诗序》中提出:“若身之所历,目之所触,发于心,著于声,迫于中之不能自已,一倡而三叹,不啻金石悬而宫商鸣也。”在他看来,由亲身所感、发于真情而成的诗歌,必然会具备一唱三叹的美感,这种美感与金石之乐的美感是相通的。在这里,诗与乐的相通之处在于形式美感带来的听觉享受,道德因素开始弱化。
“格调”与“音乐之乐”
明代中叶以来,“格调”成为衡量诗歌优劣的重要审美标准。尽管不同文人眼中的“格调”内涵不尽相同,但对汉魏、盛唐诗歌模式的追慕,内容上的不落俗套,形式上的文从字顺,是其共同特征。在“格调”这一概念中,“调”扮演着基础性角色,由“音律之美”衍生而来的“格律之美”是“调”的核心要素,“调”之美为诗歌整体美感(即“格调”)的形成提供了基本保障,所以明代以来不少文人持有“调生格”的观点。清代诗歌与“礼乐之乐”渐行渐远之后,与“音乐之乐”的关系却未有大的变化。因此,清代“诗”与“乐”的关系更多体现在诗歌与“音乐之乐”的关系层面,“音乐之乐”内蕴的形式美诉求被保留在了诗歌中。
乾嘉时期主张“肌理说”的翁方纲在《格调论》一文中有一段总结性的论述:“诗之坏于格调也,自明李、何辈误之也。李、何、王、李之徒泥于格调,而伪体出焉。非格调之病也,泥格调者病之也。夫诗岂有不具格调者哉!《记》曰‘变成方,谓之音’,方者音之应节也,其节即格调也。又曰‘声成文,谓之音’,文者音之成章也,其章即格调也。是故噍杀、啴缓、直廉、和柔之别,由此出焉。”翁方纲征引《乐记》中的文字,用音乐层面的音声之理来说明文字层面的格调之理,其对“音乐之乐”的态度可见一斑。翁方纲撰写此文的目的是对王士祯的“神韵说”和沈德潜的“格调说”进行分析。在他看来,古往今来的诗歌都具备格调,也都以格调为准则,而明代前后七子对此理解有误。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士祯对前后七子观点的纠偏,实际上回归了格调论的正途,其倡导的“神韵”与“格调”实为一回事。正是基于这种认知,翁方纲才说“上下古今,只有一格调”。
可以说,翁方纲在讨论诗乐关系时,更多是从音声形式角度切入的,抽象的道德、教化因素不再占据主体地位。强调音声的并非只有翁方纲一人,在他之前的叶燮也持有类似的主张。叶燮认为,“诗家之规则不一端,而曰体格,曰声调,恒为先务”(《原诗·外篇》)。“体格”是诗歌创作所遵循的规则和制度,属于宏观形式要素,“声调”则属于微观形式要素,体现出对音乐之美的重视。叶燮《原诗·外篇》称:“言乎声调:声则宫商叶韵,调则高下得宜,而中乎律吕,铿锵乎听闻也。请以今时俗乐之度曲者譬之。度曲者之声调,先研精于平仄阴阳。其吐音也,分唇鼻齿腭、开闭撮抵诸法,而曼以笙箫,严以鼙鼓,节以头腰截板,所争在渺忽之间。其于声调,可谓至矣。然必须其人之发于喉、吐于口之音以为之质,然后其声绕梁,其调遏云,乃为美也。”这里有两点需注意:首先,声调应“中乎律吕”。虽然传统意义上的“歌诗”在当时已不合时宜,但从中足可看出叶燮对“音乐性”的钟情。其次,声调必须是“人之发于喉、吐于口”之音。这种对声音美感的客观化认知,恰恰来自他对“今时俗乐”的考察,并以俗乐的审美效果形象化地说明诗歌声调之美。由此来看,“音乐之乐”对诗歌总体格调的意义便显而易见了。
清代“音乐之乐”与诗歌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文学领域引乐谈诗,在音乐领域也有以诗论乐的现象。徐养沅《律吕臆说·俗乐论二》称“乐之有五音,犹律诗之有四声;乐之有十二律,犹诗之有八病。不知四声不能为诗,不知八病则诗不工”,祝凤喈在《与古斋琴谱·制琴曲要略》中说“乐曲以音传神,犹之诗文以字明其意义也”,等等。这些音乐家所说的“乐”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礼乐之乐”,而是“音乐之乐”。不论是引乐谈诗,还是以诗论乐,清人都是在乐的客观化背景下进行言说的,表现出与前代明显不同的特征。清代是诗、乐关系解体的时期,这种解体主要是就“礼乐之乐”与诗之间的关系而言的,并非指“音乐之乐”与诗之间的关系。
“音乐之乐”与清代诗学有密切关系,它深刻影响了清代诗歌的美学特征,有机融入清人的诗论话语中。从二者的关系入手进行研究,可从新的视角揭示出清代诗学的独特意涵和在中国诗歌史、文论史上的价值。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黑龙江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