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对传统社会行动理论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首先,社会行动的发生场景产生了深刻变化,“网络数字场景”成为社会行动的全新场域。其次,社会行动主体的外延极大扩展,非人行动者也进入了社会行动者的行列。有学者参照哈贝马斯所说的交往行动,提出了信息行动概念。信息行动即以互联网为媒介的行动,是一种信息流形式的行动。信息行动对社会行动进行编码并转化为信息流。信息行动概念对物联网、社会虚拟现实及人工智能等传播现象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有学者认为,言语行为是一种信息行动。在言语行为中,人与语言符号的分离,类似于人与计算机语言、人与计算机程序指令以及人与人工智能的关系。哈贝马斯借助语用学的言语行为理论,建构了交往行动理论。比较信息行动与交往行动的关系,需要确定二者在言语行为层面是否具有理论契合性。
一般语用学前提
在哈贝马斯的理论构思中,语用学为交往行动提供了“一般假设前提”。语用学帮助我们确立理解所需的普遍条件,而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目的就是实现理解,所以哈贝马斯将语用学作为交往理论建构的初始条件。理解最基础的含义是,交流双方以同一种方式阐释某一语言表达。这需要双方对交流的背景达成某种规范性认可,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交流双方意向的互通。但很多时候,交流双方并不能完全实现彼此理解,词不达意、误导性表述、不真实叙述、叙事习惯不一致等情况,往往阻碍言语行为通向理解之路。一旦出现误解,交往所依托的能够满足交流有效性要求的前提则会被交往双方质疑。为挽救交流的有效性,交往双方可能就情境定义展开协商。协商的结果可能是将交流重新导入互通的言语行为,也可能因协商失败导致辩论或战略行为取代理解。在哈贝马斯的理论愿景中,协商失败是需要极力规避的。他试图用交往行动,铺设一条从言语行为到达理解的理论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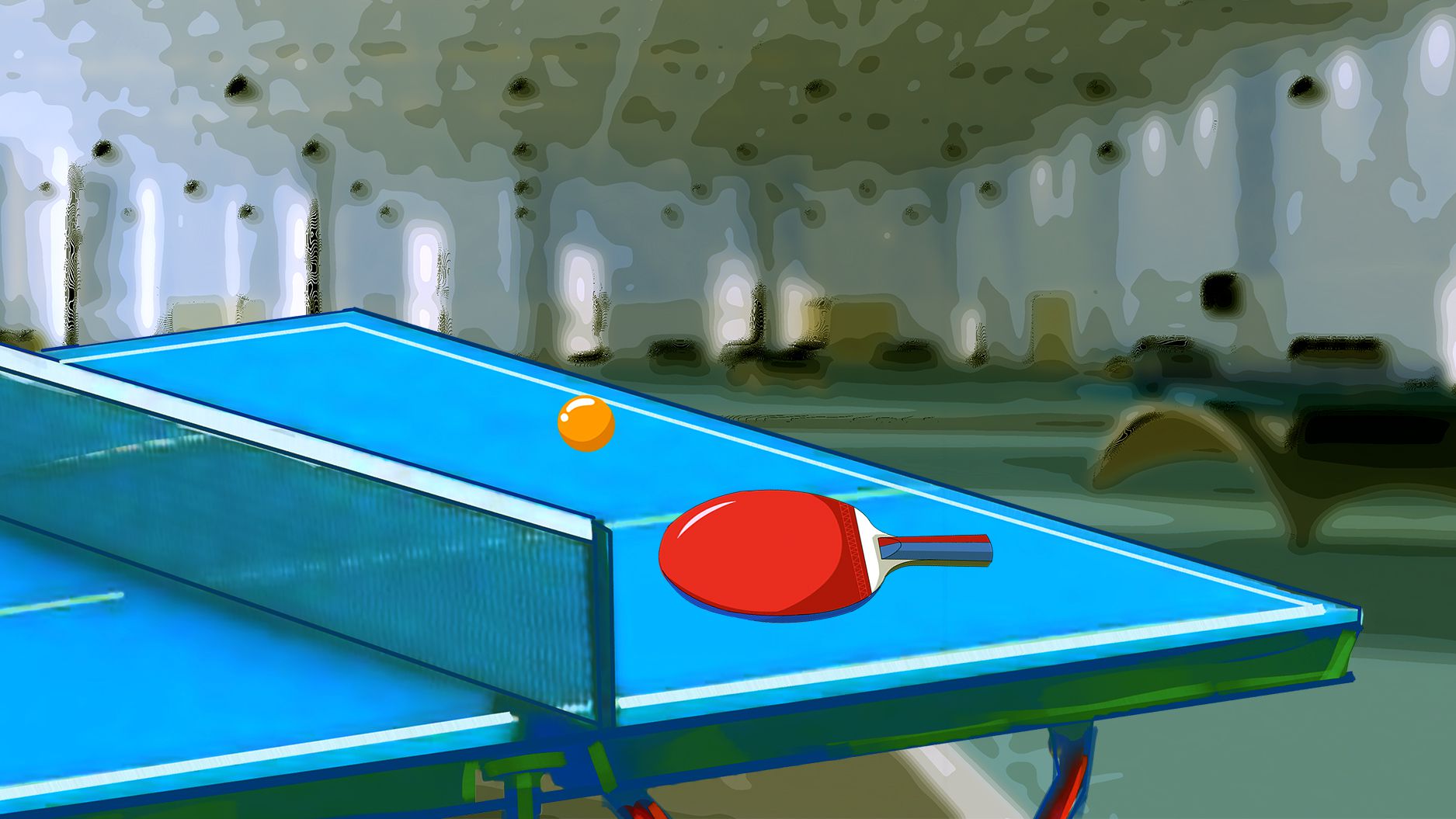 (相关资料图)
(相关资料图)
在哈贝马斯看来,言语行为具有某种“超验的强制力”,这种“超验的强制力”导致言说者自动成为“主体”。言语行为中的强制性体现在,言说者本人的言说中暗含着不自觉的假定,这些假定是理解的规范性条件。在交往中的双方,会事先假定彼此知道各自的表述有效性要求。对言语有效性要求的认可,会创造交往的共享情境。在共享情境中的交流,可以验证各自的有效性要求是否得到满足。实现有效性交流的条件包括:语法性陈述、真诚意向和话语规范。一旦言语表述及其中暗含的表达倾向能够带来真实性、真诚性和确实的可领会性,那么就可以说借助言语行为的交往实现了双方的交流有效性要求。语法、陈述和意向,代表了一般语用学意义上的普遍有效性基础。在言说者用言语行为传播时,受传者的反馈决定了传播者是否能够实现其交流有效性要求。如果受传者接受了传播者的言语行为,并认可了传播符号结构的有效性,那么交往双方就会达成关于语法的正确性、陈述的真实性以及意向的真诚性的共识。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区分了作为结构的语言和作为过程的言说。语言是一种表达性的规则系统,所有的表达形式都可以看作语言的要素。在这个意义上,信息行动也是语言的表达形式之一。交往的参与者作为有能力进行言说的主体进入交往情境,在情境中的交流体现于言语表达和对言语表达的回应两个方面。信息行动的典型形式(如网络恋爱、网络抗争、网络游戏等)都具有明显的表达与回应言语特性。将信息行动简单吸纳进言语行动,并没能解决信息行动的普遍语用学问题,也就是哈贝马斯所要确认的理解的“一般条件”。信息行动中的语用学要素,带有明显的语言学行为主义与传播学信息传递模型特点。信息的传送与接收,在传递模型中体现为符号的编码与解码。符号传播模型对交往行动的概括,不能实现从偶然性条件到先决条件的理论关联。这一模型忽略了传播者的主观意义,无法解释相互关系的意义理解和对交流有效性的主观认可。信息行动与交往行动直接的理论关联,需要借助行为主体的直觉性认识。
直觉性规则意识
信息行动以信息传播的形式对经验现象进行观察,处理的内容属于可感觉的现实性问题。而交往行动则要求行动者对预先建构的符号化现实有所理解。信息行动形成知觉性经验,交往行动形成交往性经验。对知觉性经验可以进行因果分析,理解交往性经验只能诉诸意义的阐释。对于阐释而言,外在的社会结构并不是实现理解的关键要素,符号化构成物的深层结构与规则才是意义的必然载体。信息行动在特殊网络情境下的符号表达,只涉及行动的表层结构。如果要深入符号化结构的构成规则,需要借助具有言说能力的主体的“直觉性规则意识”。这要求行动者不仅能理解以信息流形式传递的话语内容,还要对语言规则系统背后的隐含知识有所了解。行动者的规则意识,作为一种评价性机制发挥作用(比如,言说者对语句是否符合语法的评价)。
信息行动中的语法现象呈现多元化格局,不同群体对网络语言的语法有不同的建构策略。信息行动中的规则意识要求行动主体具备跨语法性沟通的能力,而这一能力在计算语言层面遭遇到了技术屏障。一般行动主体很难理解代码规则与算法逻辑背后的符号化结构原则。信息行动中的行动者缺乏一种句法识读的普遍化潜质,不足以形成一般性认知的意义阐释结构。吊诡的是,围棋对弈程序、作曲机器人等人工智能形式,不仅可以作为创造信息流的信息行动主体参与信息行动,也形成了对算法逻辑的某种结构性“知晓”。但是,人工智能对计算“句法结构”的掌握,是建立在人类行为主体编写的代码程序基础上的,并不能说人工智能具备行动者的规则意识。人工智能形式的语句合语法性与陈述连贯性,并不能形成“正确”的行为规范。而对行为规范的准确把握,是行为主体进行直觉性评价的基础。
有效性要求
哈贝马斯为交往行动设置了交往资质的限定条件。第一,言说者所陈述的命题要满足存在性先决条件,即陈述的真实性。第二,言说者要有表达个人意向的能力。第三,言说者要有实施言语行为的能力。被认可的言语行为需要与被接纳的规范相一致,并能够在言说—理解的行动关系中,指向交往双方都遵从的价值取向。在自动驾驶等智能决策的例子中,人工智能基于设定好的程序或机器自我学习生成的计算逻辑代替人进行决策。智能决策满足了交往资质的前两个条件。人工智能提供的决策依据符合陈述真实性的要求,也能够表现出清晰的言说意向。但是,人工智能的决策并不符合实施言语行为的要求。虽然人工智能的信息行动可以有效表达系统设置的规范参数,但却无法在决策中动态地呈现行动者与情境就价值取向进行的磋商,也无法通过言语行为的实施激活规范的情境意义。哈贝马斯借助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将情境规定为意义衍生的关键因素。交往行动中最为重要的不是言语的呈现性功能,表达性功能和与之相关的人际交互属性才是界定交往行动的核心要素。
哈贝马斯借语用学想要实现的是,重建主体在情境中呈现言说能力的规则系统。在情境性规则系统中,具有交往资质的言说主体有能力对话语进行解释。主体对话语的解释,是通过对同种语言之间的相似关联性鉴别而实现的。信息行动中非人主体与人类主体并不共享同一种语言,非人主体的信息行动使用代码语言,而人类主体的信息行动运用的仍然是一般语用学意义上的日常语言,只不过在信息交互的过程中被编码为信息流的形式。非人主体与人类主体在信息行动中很难借助语言的家族相似性搭建话语解释的桥梁,这使得主体在情境中的言说能力出现断裂。因此,信息行动的统一情境规则无法建立,交往行动的一般性功能也就无从保障。所以,哈贝马斯对交往行动提出的有效性要求——真实性、真诚性、正确性,并不能在所有信息行动中获得满足。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